走出濒危:赛加羚羊的命运传奇

2020 年 2 月 16 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一家动物园拍摄的赛加羚羊
文/《环球》杂志记者 张继业 实习生 王倩(发自莫斯科)
编辑/刘娟娟
在辽阔的中亚草原上,栖息着一种长相奇特的羚羊——鼻子高高隆起,又饱满地垂下,宛若一根矮胖的象鼻,让人过目不忘。这就是赛加羚羊,也被称作高鼻羚羊。因为让人过目难忘的长相,赛加羚羊成为动物界的新晋“网红”。
看上去憨态可掬的赛加羚羊,实际上是高寒地区最坚韧的荒野求生大师,奇特的鼻子可以帮它们抵御风沙和寒冷。从冰河时期走来,赛加羚羊见证过地球的沧桑巨变,其种群史更是一部在濒危与重生间反复上演的传奇。如今,这群来自远古的生灵,正以新的方式走进人们的视野。
长着大鼻子的草原精灵
赛加羚羊是偶蹄目牛科羊亚科高鼻羚羊属,是一种古老的哺乳动物,曾与猛犸象、剑齿虎一同栖息在欧亚大陆腹地,有季节性迁徙的习惯。目前,全球逾98%的赛加羚羊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境内,其余分布于蒙古国、俄罗斯等地的荒漠与半荒漠草原地带。
赛加羚羊体型中等,体长在1米至1.7米左右,肩高60至80厘米,成年后体重约30至60公斤。雄性赛加羚羊头上长有淡琥珀色的长角,环棱明显,雌性则没有角。
赛加羚羊最引人注目的大鼻子,是它们在严酷环境中赖以生存的秘密武器。其鼻子覆盖着毛发、腺体和黏液管,每一个鼻孔里有带黏膜的特殊囊,夏天能够过滤沙尘,冬天可以加热冷空气,是天然的空气净化器,让它们能在风沙、严寒中存活。
赛加羚羊不仅有大鼻子这一“时尚单品”,它们的“衣品”也十分多样。每到换季,赛加羚羊的毛发就会随之变化,夏天是棕红色或棕黄色的短毛,冬季则长出浅灰棕色或灰白色的浓密长毛,来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。
赛加羚羊的繁殖能力很强。每年11月,赛加羚羊进入发情期,雄性的鼻子变得肿胀,发出吼声,低头角斗,争夺交配权。获胜的雄性赛加羚羊可与5至15只雌性交配。次年4月,雌性赛加羚羊生产,小赛加羚羊出生仅几天,便能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奔跑。
奇妙的赛加羚羊,在华夏文明的早期记忆中曾留下过踪迹。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描述了一种异兽,“其状如羊而无口,不可杀也”。许多学者推测,这种“无口”的奇特描述,正源于赛加羚羊巨大的鼻子从正面遮住了嘴巴的视觉印象。
中国新疆地区曾是赛加羚羊重要的栖息地。然而,20世纪60年代,由于过度捕猎、迁徙路线阻隔、栖息地遭到破坏等原因,赛加羚羊在中国灭绝。如今在其主要栖息地哈萨克斯坦,赛加羚羊又上演了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命运沉浮故事。

2011 年 4 月 7 日,在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,两只赛加羚羊在快速奔跑
哈萨克斯坦国宝重生记
作为赛加羚羊主要分布地的哈萨克斯坦,为保护赛加羚羊投入了巨大心血。
20世纪70年代,哈境内的赛加羚羊约有120万只。然而,由于在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传统民间医学中,尤其在游牧民族草药与动物药系统中,赛加羚羊角被认为具有药用和保健功效,可降热镇静、补气强身和“驱邪护身”,使得赛加羚羊成为盗猎者的首要目标,遭到大规模捕杀。此外,受动物疫病、农业开发等影响,到2003年,赛加羚羊数量锐减,仅剩2.1万只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《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》中将其调为最高风险等级的“极危”物种,距离野外灭绝仅一步之遥。
危急时刻,哈政府开展了一系列保护行动。2006年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、蒙古国、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《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》框架下签署《关于赛加羚羊保护、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谅解备忘录》,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积极开展合作,畅通迁徙路线,打击盗猎行为。哈政府还建立了总面积超过500万公顷的特别保护区,并出台严格的禁猎政策,延长禁猎期限,加重对盗猎活动的惩罚,禁止刊登羚羊角广告等。
但保护行动并不顺利。许多当地居民没有工作,只能靠捕杀赛加羚羊、售卖羚羊肉和羚羊角为生,盗猎利益链顽固复杂,致使赛加羚羊的数量一直未得到有效恢复。201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,使超过12万头赛加羚羊在短短两至三周内死亡。科学家分析,由多杀巴斯德氏菌引发的出血性败血症可能是悲剧发生的起因。
面对危机,研究人员开展了更为精细的监测与研究,通过追踪赛加羚羊的迁徙路线,为恢复和管理保护区提供重要依据。与此同时,哈萨克斯坦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等众多民间力量加入进来,呼吁民众增强动物保护意识,在开展大规模巡逻遏制盗猎活动的同时,加强保育工作。
在各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,赛加羚羊种群数量逐渐攀升。202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将赛加羚羊的风险等级下调为“近危”。哈萨克斯坦境内赛加羚羊数量一度突破410万只,再次成群结队驰骋在辽阔草原上,形成一道壮美风景。
这是一个全球物种保护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功。然而,迅速的“羊口”爆炸,也给哈萨克斯坦带来前所未有的“甜蜜烦恼”。尤其是在哈西部的种群保护区,局部高密度聚集导致严重的生态失衡。泛滥的赛加羚羊还对农业造成影响,万亩麦田被啃食殆尽,农民损失巨大。此外,赛加羚羊被发现携带鼠疫杆菌和小反刍兽疫病毒,疫病暴发可能导致草原生态系统失衡,大规模尸体腐败影响食腐动物、地下水与土壤微生态环境。
面对如此情况,哈政府再度出手,从全力保护转向科学调控数量。哈生态与自然资源部近年来已批准国有企业统一实施计划性猎捕,在林业和野生动物委员会的监督下,猎捕数万只赛加羚羊。
跨越天山的友谊使者
在哈萨克斯坦为平衡境内庞大赛加羚羊种群数量而努力时,这场生命的复苏也延伸到了哈东方邻邦——中国。
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同为欧亚草原的守望者。对中国而言,赛加羚羊承载着历史悠久的美好记忆。20世纪60年代,赛加羚羊在新疆一带灭绝,此后数十年,中国曾多次努力引入赛加羚羊。
80年代末,中国从美国圣迭戈野生动物园和德国柏林泰尔动物园引进11只赛加羚羊,在新疆建立了中国首个赛加羚羊人工繁育种群基地。此后,甘肃濒危野生动物繁育中心(1994年更名为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,2012年更名为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)等机构相继开展赛加羚羊的繁育与保护工作。1997年,中国为改善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,从俄罗斯引进一批赛加羚羊幼崽。由于长途运输和气候等多重因素影响,多数幼崽不幸夭折,最终仅有一只雌羚顺利抵达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,并成功融入原有种群,留下宝贵血脉。
不同于野生的赛加羚羊,圈养赛加羚羊性情胆小,对气候和环境适应性差,人工繁育十分困难。30年来,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的赛加羚羊还不到200只,种群年均增长率仅3%,复苏之路步履维艰。
希望从草原另一端传来。在今年于哈萨克斯坦举行的第二届中国-中亚峰会期间,哈宣布向中国赠送1500只赛加羚羊。这份厚重的国礼,以两国共有的古老生灵为纽带,不仅象征着中哈之间的深厚友谊,更像是一场生命的归乡。
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,这是生态恢复成果共享与自信的体现;而对于中国,则重新燃起恢复羚羊种群数量的希望。如今,这批赛加羚羊正“蓄势待发”,未来很快就会来到中国。
至此,赛加羚羊的故事完成了一个动人的循环。它们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,在哈萨克斯坦经历了一场从濒临灭绝到繁荣的奇迹。如今,它们正以中哈友谊使者的身份,踏上新的旅程。从远古走来的羚羊,穿越冰川、草原与国界,见证着人类对自然从索取、反思到保护、协调的认知变迁。它们的鼻子嗅出旅途的方向,它们的命运折射着文明的成长。赛加羚羊的未来,将是跨国界、共担当的关于生命与和谐的新叙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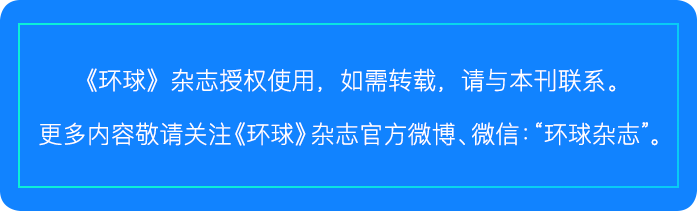

 手机版
手机版